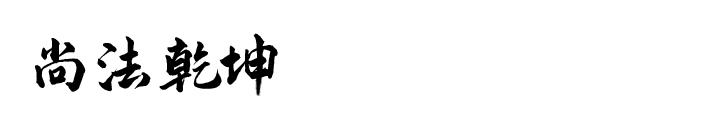乌坎事件在2011年结尾的又一次爆发和接下来的善后处理,绝不意味着类似事情会随着2011年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反思和足够的警醒。
诚如广东省委副书记在处理乌坎事件时所说,这个群体事件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只要这类事情的爆发的基础依旧存在,日后类似的事情必然还会发生,发生频率和强度只会一浪高过一浪。而这个基础就是基层权力与民争利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而农民维权的途径却极其匮乏,甚至投诉无门,权利得不到基本的救济,最终只好铤而走险,选择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以引起关注期望事情得到解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乌坎事件最终爆发之前并非没有任何征兆,相反却也历经了反映情况、上访、集会等等诉求,一次比一次激烈,最终却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件事情矛盾的最终激化固然有着农民本身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处置不当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更是多种矛盾复杂交织形成合力的结果。
通过这个事件直接反映出以下主要深层矛盾:
一、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的日益增强和地方政府人治思维模式的矛盾
现代的农民已非旧时代的农民,尤其是80后、90后的农民,不像上一代农民那样意识保守、容易满足,耐受力强,他们接受过新的教育,思维活跃,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很强,维权意识强烈。一当权利遭受侵害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权,一当维权途径不畅时,就容易走向极端。而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总还是习惯于人治,手法粗暴单一,对群众的合理诉求充耳不闻、漠然置之,甚至堵塞剥夺被侵权农民的权利救济渠道,比如诉讼难、民间调解几乎瘫痪、信访形同虚设。而一当矛盾激化就习惯性的打压,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矛盾往往会更加对立和恶化。而这些矛盾的解决本可以通过正常司法途径等法治途径解决的。
二、村民自治意识的提高和村民自治程度的发展不协调
新时代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村民自治的步伐却没有相应进步。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生效也使村民自治进入了法治轨道,一些地方性法规也对村委会行使权力做了相应的规范和限制,比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重大问题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等等。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村务不公开的现象非常普遍,滋生了贪腐,农民被少数村委会成员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积累了矛盾。农民的自治权力并没有得到基本保障,致使农村干群关系特别紧张,一些矛盾一触即发。
三、 与民争利的地方土地财政,致使地方政府在村委会和村民的土地纠纷中很难中立
我国实行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村委会行使。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卖地几乎成为村委会的不二选择。同样想要分享集体土地这杯羹的还有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程度依赖于卖地的收入。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他们就很容易形成天然的同盟,一同盯住老百姓手中的这块地,大做买卖土地的文章。地方政府一当有了利益考量,就很难在村委会和村民的土地纠纷中做到不偏不倚,对失地农民的正当诉求就很难公正合理的解决。
四、日益严重的基层对抗和司法解决渠道不畅的矛盾
社会的矛盾本应由司法途径正常解决。但是,一当涉及到征地、拆迁等重大矛盾时,地方政府唯恐司法介入,想方设法的阻止法院立案,在利益的驱动下大包大揽;人民法院也乐得顺水推舟,退避三舍。整个把农民拒之法律救济大门之外,失地农民投诉无门,矛盾只有越积越深,最后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