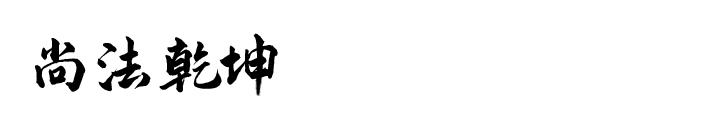在乡土社会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一些独特的对错判断标准、是非处置方法,如本案中所涉及的自诉人刘汉生逼死人后被死者的亲房叔伯要求游街“忏罪”赔礼道歉的做法。在代理或审判类似案件时,法律从业人员经常会面临“法、理、情”的困惑和冲突,如何既能依法办案,又能兼顾人民群众的基本感受,使得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能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当下的许多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实际上是法律效果的题中之意,离开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法律毕竟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她无法也不可能调整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法律从业者在法律的框架内,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也要通过先进的司法理念和良好的道德规范,去进一步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律师辩护、代理和司法人员审案、办案大抵都应如此。
一、案情介绍
2001年11月5日晚,自诉人刘汉生与张桃林发生争执,次日,张桃林上吊身亡,且身上有多处软组织挫伤,自诉人刘汉生因张桃林的上吊身亡,后经中间人的调解,拿一万元作为张的丧葬费用,并被张全胜、王社军等人扭着胳膊沿大街行至丧家,途中遭到八个被告人谩骂、踢打的事实清楚。有自诉人刘汉生指控,张全胜、王社军强迫其游街,张有莲、张未莲对其谩骂,证人赵建桢证明,张全胜、王社军扭着刘汉生的胳膊,其他被告人跟着,刘汉生脸上有血,身上有土;证人苏建红证明,张全胜、张国胜扭着刘汉生胳膊边走边打;证人杨书英证明,张有莲在骂、张国胜扭着刘汉生的胳膊;证人张和平、王起胜证明,刘汉生拿了一万元作为张桃林的丧葬费用,让他们转交给了张科学,并有张桃林丧葬费用开支单据和一万元去向单据在卷印证。上述证据和事实,已经一审庭审质证,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原审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汉生诉称八被告人的侮辱行为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侮辱罪,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查,上诉人刘汉生在返回丧家的路上,被告人王社军、张全胜扭着其胳膊,并对其进行过薅拽,张有莲、张未莲对其进行谩骂,张永林、张永正等被告在后面跟着,上述事实清楚。但诉称被告人对其侮辱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自诉人刘汉生要求追究八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理由,于法无据,一、二审法院都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之后,自诉人向中院提出了上诉,二审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采纳了本案律师康君元作为被上诉人之一张科学的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
二、本案焦点
本案的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也不存在异议,主要的焦点问题体现在:以乡土中国传统的“游街”“磕头”方式向死者赔礼道歉的侮辱行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并应该按照侮辱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自诉人刘汉生认为,“我姐夫张桃林死后,我心里非常难过,可以被告人张科学为首的八个被告人,无端怀疑我,召集众家族,强迫要求我跪炉子,无端强迫我交纳10000元赔礼道歉,非法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公然在大街上侮辱、诽谤我,在张家庄街进行游街,并进行拳打脚踢,后又非法侵入我家中对我又是打扎、又是诽谤,上述以张科学为首的八个被告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自诉人的人身权利,损坏自诉人的名誉,且情节特别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238条之规定,上述8被告人已构成侮辱、诽谤罪,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为此自诉人依法提起刑事自诉,请法院依法追究上述8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公开向自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自诉人名誉损失20000元,赔偿自诉人的经济损失10000元,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本案辩护律师经查证认为,“自诉人刘汉生一向殴打虐待其姐夫张桃林,张桃林生前也一再向其亲戚喊屈求援,而且张桃林上吊身亡的前一天晚上再一次遭受自诉人的毒打,W县公安局尸检证实死者张桃林身上皮创达22处之多,新遭皮创竟达19处之多,惨不忍睹。张桃林的上吊死亡不能说与自诉人刘汉生的殴打虐待没有因果关系。而事发后,自诉人刘汉生自知理亏,拿出钱来找人安慰被告人等,表示出了歉意。被告人没有得理不饶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豁达,把钱用在了埋葬张桃林的事情上,事后又把结余的钱交到了张桃林妻子的手里,在让刘汉生落实先前承诺去死者家中姐夫灵堂前忏罪而后又自食其言试图逃避赔礼道歉时,才激起作为叔伯兄弟和近亲属的众被告人的愤怒,致使其他被告人拉住自诉人让其兑现承诺,而这个行为始终没有过激的举动,并且后来也未发生严重的危害后果。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小街偏巷的追逐扭打行为,在距离不到500米、时间不足十分钟的情况下,再综合全案分析、结合乡土中国民间的实际做法来认定,该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充其量只能说明被告人出于义愤稍有偏激,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即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因此本案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案件办理结果
一审河北省W县人民法院发布的(2002)涉刑一初字第1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指出,“自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各被告人对其实施侮辱的具体行为,故本案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自诉人指控八被告人犯侮辱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辩护人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自诉人要求被告人返还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依法不能受理,自诉人应另案起诉。本院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科学、张国胜、张全胜、王社军、张有莲、张未莲、张永正、张永林无罪。
二审河北省H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03)邯刑终字第5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中指出,“上诉人(原审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汉生诉原审被告人张科学、张国胜、张全胜、王社军、张有莲、张未莲、张永林、张永正构成侮辱罪并赔偿经济损失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案件评析
世界如此之大,法律人所遭遇的法律困惑无奇不有,在这些困惑之中相当大部分是关涉“情理”与“法理”的抉择。情理是法理的基础和来源,法理是情理的升华和总结。“法律无非人情”,如本案展示的那样,向死者“忏罪”的情理和自诉人遭“侮辱”的法理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既有所区别,又相伴而生。办案断案讲究情理,是指办案讲究符合全体人民的情理,是普遍的情理,而非一味强调个体的情理。运用法律遵守规则,不能脱离人情和社情,要充分关照法律适用的基础,使法律真正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活”的思想和“死”的规则,尊重法律、更重情理,法律职业共同体才能够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和他人权益的裁断者。
法律为人定,本应循于人情、合乎情理。然而,法理又不仅仅只是情理,法理有时候会超越人情、高于情理,那是为了平衡利益主体的相关权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作出可能不合“情理”的选择和制度安排。因此,律师在代理相关案件时,职业素养决定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规则意识,企图通过曲径通幽大搞关系而获得额外利益,那不应是法律人的做法;努力寻找法理情之间的结合点,并成功地在个案中使法理、情理融会贯通,使个案的解决既在法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内,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才是我们法律人所应该秉承的操守。
具体到刘汉生侮辱自诉案,诉辩两方各执一词,互有证据、都有理由,最后法庭也基本认可了存在“自诉人刘汉生因张桃林的上吊身亡,经中间人的调解,拿一万元作为张的丧葬费用,并被张全胜、王社军等人扭着胳膊沿大街行至丧家,途中遭到被告人谩骂、踢打”等事实,但该事实并没有达到刑法上侮辱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程度,这不仅是由于自诉方缺乏相关证据作佐证,更是由于辩护人、办案法官充分考虑到了乡土中国的民间习惯,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和群众普遍心理感受,从而在情理与法理的抉择之间,更多的考虑到了情理方面的因素。当然,以农村地区的传统“忏罪”方式来做辩护突破口,不是说以人情为借口,无视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说更多要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司法政策的前提下,透彻地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济”的要求:宽和严之间要有比例关系,“宽”“严”要有度。该宽、还是该严,关键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好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罪而异三个原则。因时而异,即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状况即犯罪率高低而区别对待;因地而异,即针对不同地区而不同对待;因罪而异,即根据不同的犯罪人、犯罪罪名而处以不同的刑罚。(陈兴良教授语)因此,针对“游街”“和奸”“虐待”等主观色彩比较浓、乡土情理比较深的案件,若能找寻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视角和结合点,则无论是司法办案人员、还是诉讼代理人员都能比较好的应对“情与法”的考验。正所谓,“合法入情是辩点,游街磕头不为罪”。而本案辩护人有机地结合了情理法理,洞察入微,在事实和法律交会处选准了对本案实体辩护中的情节辩护,达到了无罪辩护效果,可谓棋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