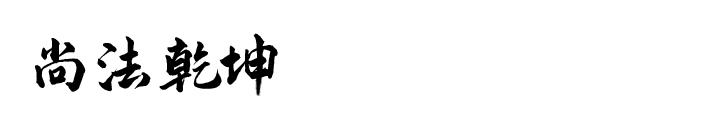人自从呱呱坠地被放逐的那一刻起,便踏上了漫漫的归途。
回 家
——乾麾
一日归来,一位女人横立在我家门口,气势汹汹地挡住了我回家的路。
“让开!我要回家。”我边说边往里闯。那人只是用手轻轻地一挡,我便被重重地摔翻在地上。
“你这流氓,霸占我的家,别想得逞!我告我爸爸去!”我被这突如的遭遇弄得不知所措,声音已染上了哭腔,“爸爸,爸爸……”
就还是昨天我血头破脸地跑回家向爸爸求助。爸爸找到那位肇事者,只在那人脸上轻轻地抹了一下,殷红的血便顺着他的手指溢了出来。随后爸爸塞给我一个硕大的苹果,被血染红的苹果好吃极了,足以慰却我遭受的所有委屈。
“傻子!你是个什么野种?居然还配有家?”那人恶狠狠地大惑不解。
“是我的,是我的,……”乘其不备,我飞也似地冲进门去找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的发现令我大吃一惊。屋里院内竟然没有一件我熟悉的东西,陌生的摆设挤塞了满眼的空间。这次不等她撵我,我便以更快的速度跑了出来,“我爸爸呢?我爸爸、妈妈呢?”我茫然不知所终。“哐啷”一声,门被紧紧地关上了,一把大锁结结实实地挂在那里。再看,那是什么锁?分明就是一具头顾,似乎要笑出声来,我脑际闪过一片可怖的空白。“我爸爸妈妈走了!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那不是爸爸、妈妈吗?”我惊喜地发现他们两个就在不远处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兴奋地一边、一边追。可是他们似乎一点也没听到我的声音,走的很紧。我怎么追都追不上,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朦胧的视野里。
狂野的风夹杂着腥味铺天盖地、漫卷过来,我打了个激灵,下意识地裹紧衣服,可是却发现我身上竟未着一物,连鞋子都没有。我想跑,可怎么都跑不动,似乎被什么钳住一样动弹不了。
温热的光熏暖了我的头发,力量又开始充盈着我的血液。天已不早了,得赶快回家去,我急匆匆地走着。
“喂!走那么急干么?我们一块走好吗?”有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这声音似向我传来,是谁呢?我循着声音望去,不远处伫立着一位美丽的姑娘、闪着忽幽幽的目光,怔怔地看着我。在这荒郊野岭一个人步履匆匆,怎比得上两人结伴而行?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
原来她也是要回家去,不想迷了路在这儿遇上了我。她给我讲述了她的经历,曲折感人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不由得潸然泪下。皎洁的月色静静地泻在我们身上,不远处的嵩草凄凄悲悲地絮叨着什么。那是谁家的灯火在远处忽隐忽现?映着她脸上晶莹的泪珠迷离闪烁。风骤起,把我们紧紧地裹在一起,一切都睡着了,我们相拥而眠。
待我醒来时,竟发现自己睡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旁边还酣睡着一位陌生的女人。我吓坏了,急急忙忙趴起来,扯起衣服准备逃跑。可那位女人醒来了,亲昵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躲闪不及、穷以应酬。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误了贵宅,对不起,我要回家了。”
“啊!你要往哪去?你这个没良心的。”她惊异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哭声都急出来了,她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这是咱家!我是你的妻子啊!”
“妻子?妻子?家?……”我惊愕不已,恼怒地把她的手捋去,“我什么时候有的家?脑子里一片空白。
见我不信,她翻出了厚厚的一摞证件指给我看那上面果然载有我的名字,还留着我的笔记。铁证如山,我颓然坐在地上。
吵嚷声惊动了四邻,他们纷纷赶来劝解。忽然我发现我的家就是隔壁,我的妻子从那边过来了,这下可有救了!我急切上前握住她的手。
“救救我吧!我不是成心这样的。咱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咱家去吧。“
“你!你怎么能这呢?”她警惕地挣脱了我的手,就象对任何一个不怀好意的人一样。
“你!怎么这样忍心?昨天我们在一起还好好的吗?为什么今天这样对我、形同路人?回咱家吧!”我声泪俱下地哀求她。
“怎么能这样啊!?……”众人议论起来了,但大多夹杂着对我的鄙夷。“真是混帐、流氓……“有的人竟然气愤地骂出声来。
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我隔壁的妻子终于举家迁移,远走高飞了。临行前我并没有放弃最后一次挽留她留下来的机会,苦苦央求她把家留下。她只是本然地望了我一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别走!别走!……”我的心似乎被绝望与恐怖掳掠而去。身子骤然间变得同僵尸一般,似乎被什么东西箍得越来越紧、不能动弹。啊!是几条蟒蛇!吐着腥红的信儿在我脸前晃动。我惊骇到了极点,拼命挣扎,出了一身冷汗,再看左右,哪有什么蟒蛇?一位陌生的女人安然地躺在我的旁边,睡得正香,被时间剥蚀的美丽还残留在她憔悴的脸庞上,依稀可见,一只温润如玉的胳膊搭在我的身上。我惊魂未定,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雨,下起来了,和着凄惨的音乐、撕撕扯扯,从天而降。凄历的号啕声执拗地缠着我久久不放。“让我回家吧!天啊!”我捶胸顿足,凄怆的呼喊声响彻云霄,我陷入无家可归的巨大悲恸之中。
幽暗的夜色下走过来一个人,温文尔雅,对我说:“走吧!你没有了小家,可总有大家吧,眼我走,我会带你回去的。“
我并不太相信他的话,可还是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一言不发地在他的身后,直到我被带到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发现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我才感到一些轻松。
第二天,我和几个人坐在一个台阶上,静静地等着那个人的出现,气氛肃穆而凝重。昨天带我来的那人终于出现了,一时间竟变得凶神恶煞,丧心病狂。他把台阶上的人挨个叫下去连番非难、拳打脚踢。片刻间伏尸一片,连台阶上的石头都渗出了血。最后轮上叫我时,我强作镇静地应对着他的种种责难。
“你还要回家吗?”
“当然,没有谁能拦住我回去的!”
“你难道没有看到他们为回家而付出的代价吗?”他指了指横在脚下尚在淌血的尸体。
“我不怕死,用死吓我有什么用呢?虽然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我坚信他们都已回到了家。”
结果那人言不由衷地说:“好!好!这正是我想要的答复”他上的肌肉在抽搐着,边说边往后倒退。
突然他被一辆急驰而至的大马车夹在了车辕中,幸亏车夫采取了紧急措施。然而那人未离险境便撒赖、非难车夫,恣意纠缠。突然车闸松了,车急驰而去,一场骇人的血灾发生了。那人被辗得身首异处,血肉模糊。那颗被辗下的头在痛苦挣扎着,张大嘴急剧呼吸着,瞪着眦裂的眼睛。一会儿又和痉挛滚动的躯体搅在一起。飞血横溅,旁边的一个孩子满身血污,孩子的母亲疯狂嘶号、撕心裂肺。我魂飞魄散,苍慌离去。
耸起的山壁间仅留下一条侧身可过的羊肠小道,偶或至空旷处,一边的山壁似乎是在恣意地倾斜,把天空都挤弯了,突出的山岩犬牙交互,似乎时刻都会掉下来。我没命地逃,又进入了一个幽深的洞穴,到处是漆黑的一片,我艰难地摸索前行,屏息蹑足,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忽然一丝光线窜了进来,闪烁不定,渐渐地愈闪愈亮,如跳跃,如舞蹈,似燃烧的火焰,似欢悦的音符,……,深深庭院,幽幽兰香,……